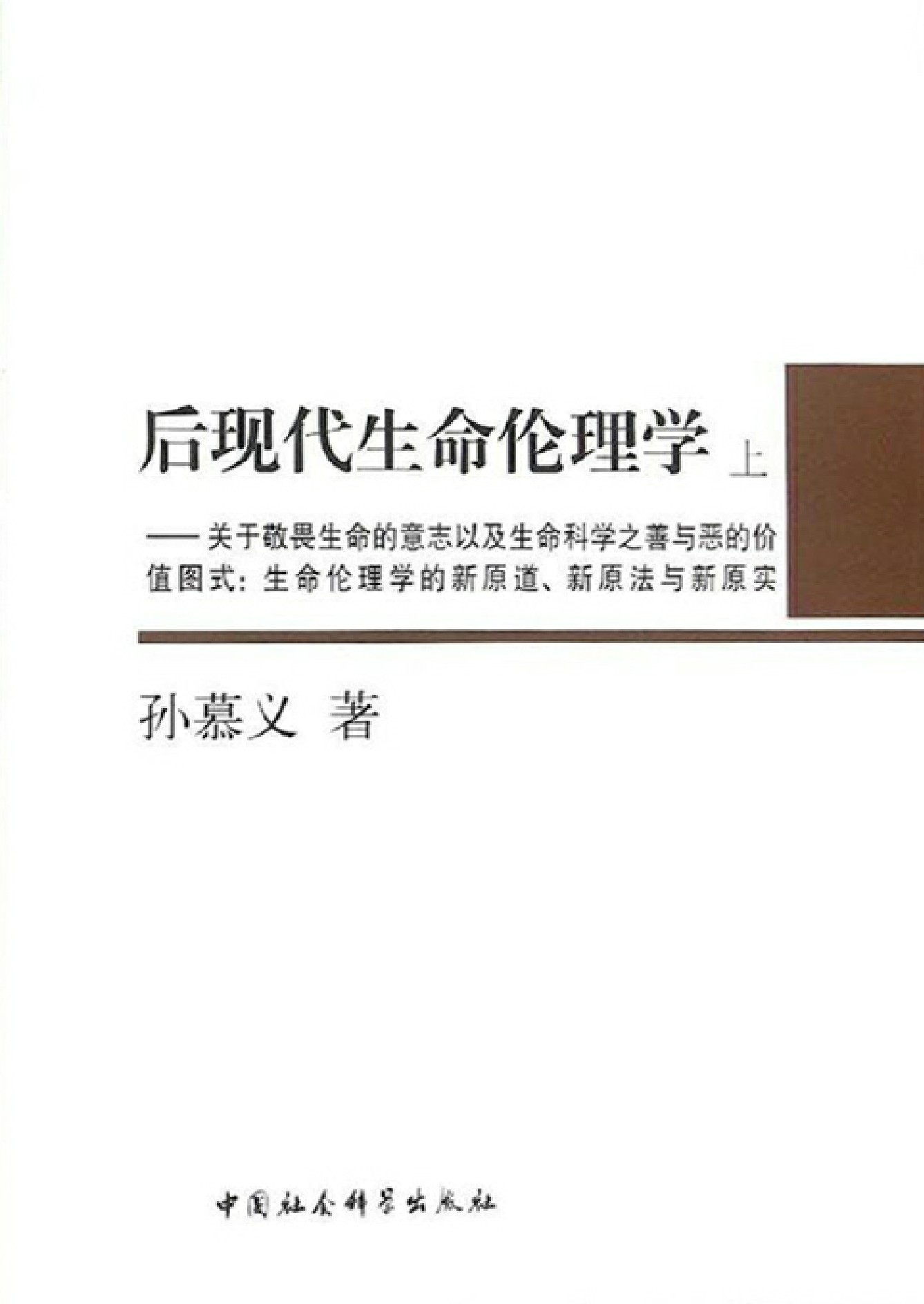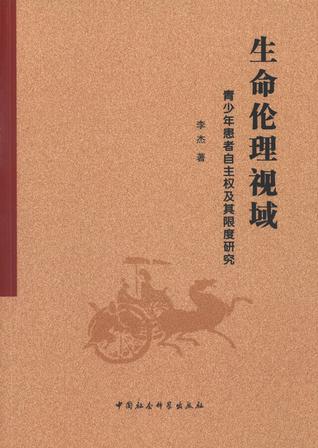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录
孙慕义我们生活在人们对任何事物不再确信无疑的时刻,我们原本担忧的很多有关信仰的问题,真的全都发生了,所以,这个世界异常清醒,又异常困惑与混乱。因此,很多人幻想能够追回人类的那种虔诚与执着,逃离金钱与物质的桎梏,即使是游戏,也要有道义的限制;关于自由,不可以过度情感发泄,最危险的是,甚至使其成为我们身体存在的基础;因为毕竟,理性还静卧在我们身边喘息,并告慰或者警示我们:前面,可能就是生命的陷阱!起初 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记1:1-2)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经 第一章)事原本就是“空无”,但正是这一段从未有的空无,给了我们万有和以我们理想化上帝赐予的万能,何以使我们人类欲望达至我们预想的“至圣至善”,就是因我们所处的眼下这个人类世界,有时,太使我们失望和压抑,我们几乎没有在空无的时间与空间加添我们预想的物如与“自体”,我们本当应该风华璀璨或者真善美的世界,显得如此遥不可及或几乎不可实现;我们本应该的振奋与高远的情志一直遭遇着阻遏或消解,超载的物质诱惑,为人类贪婪的本性或原始的罪性,浇注了燃点的油柱,星火来兮,无可常安。因此,被无神论者贬斥的宗教,竟然一时间,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炬,点燃了人类又一种希望和期盼,那就是理性与信仰之火,这就是黑暗源面的万物之母,生命从来没有过的以其灵、其妙、其徼、其圣道,以及其伦理之大义,为我们所永恒之求索。我们以从没有过的信心,能够承继源于“信望爱”原初生命的招叫、附丽于这生命伦理的精灵。在此,我并不想过多地叙述我和我的学生们制作这部译稿的心路经历,或是专事表白为什么我坚持把这部沉静、艰涩、厚重的思想巨作介绍给我们中国的学界和读者;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当前太需要生命政治和身体伦理的学术精品,在我们以往走过的这段医学人文学历史过程中,我们很少有机会邂逅针对能称其为人类文化心语、格调高蹈、思想深刻、视界开敞的文化巨制;在这潦草的年代,可以以此使我们育成能够鉴别那些仅仅引起文化快感的学术垃圾的能力,以此抵制那些市井有毒的快餐,它们已经侵蚀我们曾经充满清纯和本真情愫的灵性家园。作为思想、学术与情志的朋友,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是我在西方世界少有的知音并能够进行思想与情感对话的友人,我们交往有限,但那种心怡相连与文化偏爱,几乎使我们一见而如故交,不能忽略的当然是信仰的原因和人生境遇,以及家族传习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学术观念和学科的追求和共同的道德共认意识,如此方成就我们今天这一具体的项目与合作。他的整全道德理想与真全生活的祈盼,唯有如此深刻理解他内在世界指向的人,才可真诚地透悟并宣表他的希冀和愿景。恩格尔哈特教授是当代美国乃至世界上具有超凡学术功力的、卓越的生命伦理学与哲学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是东正教神学家。长期以来,他贡献给我们近20部生命伦理学与哲学专著、著作和200余篇学术文章。他的睿智与学术穿透力,在生命伦理学界很难有人与其相比,也因此赢得了学术界普遍的赞誉,并已经足以作为当代世界医学人文学领域的主角。夫有志,当孝其才。我们这一代学人,其实已经遗失了前辈许多优秀的传统,仅对照清末民初,或是五四前后的学界先锋,都可说是一种倒退。核心是因为如此误会的学术文化体制和人性逐利的风尚,挤压了学术责任与知识界的基本信仰,我们常常在“我非我”的冲突中被灵与肉绞杀和搏斗吞噬;而我们这些人,如何在通过痛苦的历练后回归于原初的那份天真和性本善的自我,可以学一下这部书,接受斯人的智慧和独到的点拨。我生自然还是我身自然,本为身自然、物自体,身物本色而人生可化之为超然。人应临世风道而勿戒本道,只有炼狱苦行后,才可皈依真理的本道,太多的诱惑与生命的杂陈,亚当之后漫长旅途的劳顿与怨怒,由此平息,圆我们最初的渺远的心愿,只是为,最后,无愧于我们的艰辛,无愧于我们的盼望,无愧于我们的信仰与圣爱。现在我要说的是,本书显然深化了先在出版并已经在中国产生影响的那部《生命伦理学基础》,而且是一种智性的超越,那部书的开启是在20世纪70年代,写就于1995年;距离本书的写作整整跨越20余年,也就是说,作者从青年时期走过,随着世界后现代风云霍起,其学术和学科体系构思以及学术思想核心已经形成,并臻于成熟。因此,他以伦理神学(严格来说应为东方正教伦理神学)的角度,集合哲学、身体伦理、生命政治和医学的知识维度,对生命伦理问题,做了一个宏大的巡览与审视。与前一部书不同的是,他已经寻找到了俗世生命伦理学尝试“整全道德生活”失败的原因,他终于还没有放弃他和他的同伴对于信仰的追求,和对于灵性的敬拜;也就是说,在这部以基督教神学解读的生命伦理问题的长途远行中,他以最后的“上帝”信念保留了自己作为基督徒的思维逻辑根基,并且排除了所有世俗的干预,返回了最初出发时的耶路撒冷城墙,虔敬地聆听以斯拉的声音。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哲学的解决途径和神学真理是协调一致的:真理就是那人(a Who)。这时期的神学是人们在苦修过程中,通过在上帝面前祷告忏悔而获得的。在这样的神学理念中,生命伦理学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只有接受邀请进入神的人才能获得生命伦理的知性。对于欲回应‘我怎样才能获知真理?’的人,首先要接受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在禁欲苦修中转变。这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最终,世俗道德无法解读明显自洽的、唯一的以及为理性所确证的道德文本。”他在对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以及克尔凯郭尔的主张的分析之后,认为:“世俗道德并不能替代宗教伦理去维持它自身不能维持的道德。世俗道德不能提供一种规范的世俗生命伦理学……”鉴于如是,我们中国的读者就将遭遇一个难以回避的“上帝问题”。上帝的概念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理解“上帝”,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个“神仙”、“天”、“佛”或“道”的对应,但这与西方的上帝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的上帝是与其民族血液成分融为一体,并不自觉地影响人们的世俗生活,比如对于疾病、医疗、生殖或死亡问题的态度和选择。上帝问题不在仅仅囿于教会的灵性生活,而且在阿奎那之后,就成为哲学的一个部分,并将人类各种处境,作为上帝某种方式的、有指向的有效言说。这在瑞士神学家海因里希·奥特(Heinrich Ott)汲取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思想,创造了“位格有神论”的思辨语言之后,就使人们有了一个崭新的、富有存在哲学意蕴的关于上帝的理性认知,同时,对传统理智主义的自然神学与科学神学有了一个很好的接应;也针对后有神论、即“上帝已死”神学与“无神论宗教”,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圣经观,这种既非自然科学又区别于历史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解救了当代或后现代基督教的文化困境;建立在位格观念上的“对话神学”、“祈祷神学”,则帮助诸如恩格尔哈特这样的具有浓重宗教意识和情感的学者,厘清和梳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初步织筑体系化理论,并能够重新自如地游刃于哲学、宗教、科学和生命政治论之间,给我们以特殊的、合理的、自恰的理由,教我们无嫌疑地、睿智机敏地处理医学生活中诸多的复杂关系。尤其当我们深陷于两难的伦理窘境之中时,信仰和灵性就能够给我们以方向和解决具体伦理问题的美善、灵便的方法,我们则不必因认识的冲突,被仄逼进狭窄的悬崖幽谷,或承担道德的风险。其次,本书的意义,我个人以为,不仅仅在于生命伦理学理论上的突破,开阔我们的学科视域,而且,将其理论和思想置于汉语文化语境中,可以使我们体味生命伦理学的神学核心本质和基督教转移基因的结构,帮助我们真实地进入西方生命伦理文化腹地,与西方学者进行深入的对话与交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中国文化中的神圣观念非常含糊和无力,表现在这种文化在历史中几乎从来无法感受到一种能与之进行真正对话的“他者”(见海因里希·奥特《上帝》,朱雁冰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作为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就有必要理解上帝这个概念,并能够回答出为什么恩教授坚持,在临床治疗学中,宗教因素能够完成医疗技艺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通过宗教的感悟和体验,疾病才能获得完整的“治愈”。同时,我也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作为汉语文化圈一个新的生命伦理学时代的开始,并修正我们这些年来对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误读,改造我们的生命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活,澄清我们许多糊涂的学科观念,争取成为理智的、清明的学者;若能圆此愿,我想,这是最使人欣慰的结局。具体说来,恩格尔哈特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是为了与世俗生命伦理学区别,提出这个用基督教神学解决生命科学技术难题的学科,它的两大部分构成是: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形成,学科地位,与世俗生命伦理学的平行关系,信仰、上帝等道德神学概念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影响,传统宗教伦理学和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关系;生命科学技术与基督教伦理学,用神学的视角研究生命、死亡以及生存状态等问题。当然,恩氏还没有与逻辑组合更加相关的全部理论,但他的思想已经臻于体系化,也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概念,除对于道德异乡人、允许原则等概念的续用外,他在本书中,还建立了道德共认意识、真全生活等;并对整全性道德予以极大的充实。本书作者有渊博的知识背景,能够自如地驾驭经典的道德神学或伦理学语言,对于基督教思想历史和东北欧、南欧诸多民族的民俗与典故,信手拈来,令人折服。恩教授又是一位富有浪漫气质、翩翩风度的大学者,其文字与其演讲时激情四溢富有感召力的神采一样,每每冲击人的思想神经,尤其再加添东正教神学家传统的深邃冷寂的哲思,则更会给人以心灵的长久震撼。普遍的哲思和把多态的世俗概念镶嵌在物质的世界中,并亲身参与凝视与反省;随后,冷静地思忖生命的基督教道德问题,概如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并且只有通过基督教的语言,我们才可以真正读懂他的思想与主张,以至于我们中国读者与生命伦理学界,将会通过此书,纠正视之为“极端的基督教伦理学成就”的观念。长期以来,对于汉语文化圈的生命伦理学学者们来说,始终认为恩氏不过是带有基督教情结的美国另类生命伦理学家,他的情感冲击力不过来自他的宗教情结以及才思和睿智,很少有人沉入进深层研究他丰厚思想的成因。作为东正教虔诚的教徒,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研究不过是他信德行为的一部分,处于一种转移的信仰,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世俗的伦理学语言倾诉他对生命的爱和渴求;他爱这世上的人,他更爱他心中的那个“上帝”。因为没有基督化的语言训练,我们中国的学者、包括自认为他朋友的人,并不理解他的生命伦理学最后和道德神学本是同根生长的学问,那种内在的、隐藏的、压抑并随时等待释放的思想潮水本来源于他虔敬的基督教信仰,没有这种真诚的语言认知,将无法消化他的作品和演讲,尽管他到处受到很多人的奉迎。译完此书,我更以为,用道德哲学和伦理神学的融合方法研究医学与生命科学问题的当代学者之中,应以恩格尔哈特为最重要的标识,他当之无愧为此领域的第一琴手。生命伦理学最后成形逾四十余年,极其缺乏毫无保留、勇往直前、同时不在意任何外在利益和权势威胁与诱惑的学者,没有基督教精神,这样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我们许多人在台上慷慨激昂,陈明自己通过舶来别人的思想与刚刚学到的观点,以为真的达到了生命伦理学的顶峰,并不允许不同意见的人提出与之不相符合的声音,那种霸道与幼稚,玷污了本属于基督神学的生命伦理学的圣洁与沉静。而恩氏的深邃的思想可以教诲这些人认真反省。健康保健,是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命题。当人们去捕捉具有新闻价值和吸引公众眼球的克隆人伦理争议问题时,却没有意识到健康保健这个最普通但又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存在必须有一个好的医疗和保健作为前提;与平民和大众分离或远离的新异问题尽管带有刺激性和戏剧感,但它们却不应作为我们倍加关注的现实。医疗公平是生命伦理学需要研究或讨论的问题的中心。可以说,没有宗教情感的学者经不住世俗话题的诱惑,也不可能获得冷思之后的思想成果。当然,传统基督教在处理拒绝治疗、过度医疗、器官移植、堕胎、身体增强术、给病人提供医疗辅助自杀以及对病人实行安乐死等病例时,其在心理矛盾和宗教信仰冲突中所采用的方法,似与医疗保健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却和世俗伦理一贯所持有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恩格尔哈特做了杰出的理论开拓。基督教有关流产、杀婴以及人对死亡的操作等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有关使徒的记载。罗马天主教对于健康保健的思想有着坚固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回顾到几个世纪前。提涉此类问题,还有本书中其他的历史记载,都是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展现出来的。如同所有的历史记录一样,这里提到的话题也承担着本书作者的责任。我们必须有一些关于现实的基本特征的假设或承诺才能从繁杂的事物中获得信息。每个人必须知道他大体要寻找些什么。任何一件事的确定都必须依赖人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事物。恩氏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从自由意志世界主义(或自由论世界主义)过渡到自由世界主义,并以自由世界主义稀释原有的所谓“公共理性”。超越“自由意志”的传统,实际上,就是从对道德异乡人的简单允许,过渡到去神圣化的自我决定,以及一切生命的自主的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并彻底埋葬道德“帝国主义”,建立个性解放的伦理机制,最终回归或再造一真全的理想天国。他精致地审视了当代世俗化医学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人对于身体康健和幸福快乐的期盼,从大公主义传统引导我们的政策方向,最后具体关照身体的现实利益和基督徒式的灵性救赎,这种巧妙俊美的构思,确是令人惊叹。视角有时决定结论。一段历史对某人来说是道德颓废的历史,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道德进步。关于生命技术和死亡问题的争论,如果用发展教义学的视角去判断和观察,我们也许就不再只知道指责和抵制;而会持一种平和的心理去考察问题: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些技术和手段可以解救人的生命,并作为健康事业的一个部分。当不同的历史记录承担着不同的伦理神学义务时,这种不同就像是物理上具有分歧的记录。恩格尔哈特举例说:“透过物理镜头,亚里士多德、牛顿和爱因斯坦眼中看到的宇宙是多么不同啊。”H .Tristram Engelhardt,Jr:The Foundtions of Christian Bioethics,p .8.恩格尔哈特认为,19世纪末期出现并在20世纪50年代风靡罗马的天主教医学伦理手册和道德神学概略与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一脉相承,并延伸到16世纪初期和西方科学的繁荣时期,这时的西方科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医学和它的基础科学。从16世纪向前看,文艺复兴后医学令人瞩目的进步,促动着道德神学也对医学产生了兴趣。鉴于对医学的信心,甚至连笛卡尔都相信他的生命能够延长。虽然医学带给人类的益处还没有所说的那么多,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人们稍后才能看到治疗效果,这种知识的进步也是惊人的。科学和医学研究对医学新的说明改变了医学知识本来所包括的含义。恩氏追索历史认为,相比之下,人们仿效特伦多主教会议(1545—1563)成立了一个和罗马天主教神学思想一脉相承的组织,它一直完整地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前经院时期到经院时期,罗马天主教道德思想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前经院时期是田园风格的,它的神学精神更接近于教会的第一千禧年精神。经院时期以散在的理性思维和系统化为标志,开始于12世纪并延续到特伦多会议时期。始于特伦多时期的现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经院的传统,并使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正是这个时期人们将所有工作都集中于对医学的思考,并形成了道德神学的子学科。特伦多主教会议以后的思想、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道德神学的思想都非常具有洞察力。它远远不是对以往思想的机械应用。罗马天主教医学伦理学思想和学识的重要特征是形成了一个单一的连贯的研究团体。参与团体的人都要遵守一些共同的意见、假说、程序或法则。另外,他们对于谁具有道德权威去解决道德纷争有共同的理解。纷争时有发生,也的确在发生着,但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能控制住自己。为了引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有关科学革命的隐喻,罗马天主教医学道德神学家采用了共同的范例。他们不理睬道德思想的危机问题,而对世俗道德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感兴趣,并因论争道德基础的不同而闻名。恩氏认为,我们不要害怕做出一些基本的假设,同时也要大胆自信地应用一些基本的原则。道德推理的大体框架和假设不但不会产生问题反而会激发人们去探询一些特殊问题,解决方法是基于对道德科学本质的理所当然的理解。我们会遇到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引起危机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罗马天主教才普遍开始了基督教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正如约翰·伯克曼(John Berkman)所说,从神学手册上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到道德神学的连贯性思想,1905年的手册上支持的基本思想结构和类型在1605年的手册上就出现了。道德神学的思想信心十足地足以回答新科技进步所提出的问题。如此透彻和具有穿透力的研究,在全球的生命伦理学界是罕有的;深思起来,这足使我们折服。恩氏在独立的研究中注意到,其他一些因素也使得世俗生命伦理学比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更富有吸引力。文化的世俗化使人们失去了把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当作道德的指导来源的兴趣。对传统道德权威形象的依赖如果不是一种错误意识的表达则被认为是变坏的家长式作风。权威差等意识下传统基督教认为的社会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多元的这种思想是十分愚蠢的。认为宗教传统绝对应作为道德判断的来源的想法与新兴的自主性和个人权利的想法发生冲突。事实上,传统的基督教不仅等级森严而且家长制严重。它十分重视圣保罗的以下宣言,“男人是女人的领袖”格林多前书 11:3。和“男人不是因为女人创生的,而女人则是因为男人创生的”格林多前书11:9。。即使基督教认为只有接受男女平等才能获得救赎,传统基督教仍为他们的等级制度感到是一种不可丢失的荣誉和威严所在。与20世纪60年代权利运动的背景和它们对社会权威的传统主张的反抗相反,传统基督教的对事物的理解既让人不可接受又让人觉得尴尬,甚至于被人们断然拒绝。这些观念表述在基督教界的道德观,并且直接控制和决定了生命伦理或性伦理意识。生命伦理学诞生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基督教的承诺是对人的自主权利和人性的压制,因此在传统基督教和后传统基督教之间出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德沟壑与生命伦理研究的文化楔入点。传统和后传统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割裂性的分离使基督教道德变得更加多元化。西方基督教改革的多中心和后现代化,形成了道德的多样性格局,这一点在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中长期得到了体现。传统和后传统基督教道德观点的差异使这种局面更加复杂。使一些后继基督教宗派定位和划界比分离这些宗教更加困难,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主教派Episcopalians 即英格兰圣公会,在英格兰被定为国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称为英国国教会,而改为某国安立甘教会。和长老派Presbyterians是英国清教徒派别之一。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制管理教会,要求国教进行加尔文化的改造。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该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曾一度构成国会中的多数派。后被独立派清洗出国会。,发现他们对道德和生命伦理学的理解比他们对于自己宗教的更加开放的神学家和同行的理解更能取得一致。尽管一般人都鼓励对传统的叛逆,一个思维困惑的医生在寻求道德指向时依然会遇到诸如基督教道德多元化理解的困扰。无人清楚哪些基督宗教派别能给予医学道德选择清晰的向导。例如,罗马天主教和新教在考虑到避孕法、绝育和辅助生殖等时,在什么行为和决策应该是道德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西方文化日益世俗化的今天,我们也很难理解哪些选择符合自认为真理的教义。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就在于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进行研究与清理,获得既尊重传统又尊重个性,也适应于文化背景、不伤害社会与人的尊严的结论与方案。这就需要从伦理神学的每一个细微的节点去深入探究,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即是最好的道德哲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生命科学的集合。在多样化的年代,当考虑到信仰的不一致真正带来了危险时,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或至少说成是传统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出现的差异是很发人深省的,这就产生了对我们这一学科理论构建的阻碍。西方宗教战争史和严酷的高压政策制约了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因为信仰与文化的原因,传统基督教生命伦理主张在当代面临质疑。在一个习惯于应对差异的成熟的社会,对待像堕胎、安乐死、克隆人、同性恋这类问题,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主张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基督徒和另外各宗派、甚至异教徒都分开,各自评价取舍的道德理由,分成世俗与宗教两个序列,制定两个根本不同的选择标准和善恶评价体系。这显然是可笑的。这不仅不能达到顺应历史和人类进步的目的,而且会进一步扩大人类的分歧或冲突,在文化和市民生活中,甚至在家庭内,造成极大的混乱和不稳定。这样会危害到和平社会的构成。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特殊内容使得它与容忍为敌、与冲突为友。曾经造成过去基督教战争的基督教在20世纪中期,正在形成未来的宗教战争或与宗教相连的文化战争。考虑到一些后传统基督徒的观点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权利运动,传统基督教都表现得最为反动。它拒绝进步论者将人们和社会结构从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主义的观念。他们认为流产、避孕、宽容同性恋的社会风气不是解放的方法而是通向诅咒之门。传统基督教并不欣赏那些似乎是从已经将女人屈从于男人的生物学力量中解放出来的价值选择,他们认为,“通奸的性革命”、避孕的世风、流产都只不过是他们带来的情欲宣泄和道德混乱的进一步发展。基督教内部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更加深那个时代的道德混乱。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不是提供一种解决生命伦理学争论的途径,而是在考虑到健康保健政策后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引入更多的思考,并且创造出使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事业如何为最大多数人实现最大幸福的理论。恩氏认为,当基督教生命伦理学面对为新时代的高技术医学提供道德指引的挑战时,发现自己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多重的困难深深地扎根于当代基督教。基督教被划分为多元的基督教;它无法提供确定的向导。一个人为了赞成他想要拥护的行为可以不选择束缚更多的宗教观点来进行解释。例如,有人想为有捐赠人的人工授精找到合理的宗教解释,他只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基督教神学家。一些主要的基督徒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基督教的信仰也不能够给予确定的指引,因为用数世纪前的老方法来解决道德纷争已经被放弃。比如,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曾有为当代健康保健政策提供指导的机遇,但是它似乎搞不清该提供什么样的道德规范。结果,现代社会的基督教的合理性只能引起人们的怀疑。如果这种情况还不算太糟,周遭的文化甚至有数条理由认为基督教是开放的民主政策的威胁。首先,传统基督教是在等级体制中寻找解决道德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个人推理和摆脱过去的束缚无拘无束的选择中寻找解决方法。其次,基督教的等级体制是家长式的。再次,因为它在道德上的特别承诺,基督教强调差别而不去鼓励形成大家一致赞同的道德规范。最后,到目前为止,基督教提供的道德与世俗道德形成了对比,它不能为战后西方多元化的世俗社会的公共制度或政策提供指导。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基督性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必须进行理论上的改造或者重新创制,如果不汲取哲学成就和后现代文化的营养,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是没有前途的。在此,也是恩氏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发轫的缘由。恩格尔哈特最先致力于消解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与世俗生命伦理学的差别。为了弥补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太过于基督化的困难,很多基督教道德神学家将注意力放在显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和世俗生命伦理学在精神上不存在差别。耶稣会士道德神学家约瑟夫·福克斯(Joseph Fuchs)推论:“……基督教和非基督教面对着同样的道德问题,而且……他们都要通过人类真实的思考和规范来寻求解决方法;比如,通奸和婚前性行为是否是道德的或者在道德上可以被允许,世界上富裕的国家是否应该帮助贫穷的国家以及帮助到怎样的程度,什么形式的生育控制才体现了人的尊严。这些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的教会和其它人类组织总是不能达成共识,这不能归结于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之间存在的道德差异这个事实。”Joseph Fuchs,”Is There a Christian Morality?”in Readings in Moral Theology No.2: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ristian Ethics,eds.Chaeles Curran and Richard Mccormick(New York:Paulist Press,1980),p.11.詹姆斯·瓦尔特(Jams Walter),另一位认为世俗的世界和基督教的本质一致的神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的论点是在道德规范这个基础上,基督教伦理既没有任何特色又没有特别之处。” 以上二人的主张与西方基督教自然法导向、道德的神学思考大体一致,说明了基督教道德把自然法则显现和表述的原因。有了这些分析的基础,基督教道德神学和世俗道德哲学之间的道德差异消失了。基督教伦理,我们认为的(1)多元的,(2)与世俗伦理不同,(3)通过强调道德差别而产生使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分离的危险,可以通过推理与世俗伦理的本质相同的认知结成一体,并证实了全人类的道德。正如查勒斯·科兰(Charles Curran)所指出:“显然,一个人认为耶稣是上帝的认知至少影响了他的意识和他意识的主要思考,然而基督教的和明确的非基督教的能够并已经形成了相同的道德结论,能够并已经分享了大体上一致的道德态度、意向和目标。然而,明智的基督徒在近似的道德态度、目标和意向上不武断,这些包括自我牺牲的爱、自由、希望、关注邻人的需要或是认识到人只有在生命消失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的生命。明确的基督意识的确影响了基督徒的判断和他做出道德判断的方式,但是非基督徒同样也可以并已经获得了同样的道德结论,同样也可以赞成和珍视那些基督徒从前错误地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做到的最崇高的动机、美德和目标。凭着这些准确的判断,我否认存在特殊的基督教;也就是说,非基督教的也可以而且已经得到了同样的道德结论和珍视基督徒同样珍视的意向、目标和态度。”Charles E. Chrran,Catholic Moral Theology in Dialogue (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6),p.20. 许多其他基督教道德家也详细阐述了基督教伦理和世俗伦理之间本质相同的观点。鉴于这样的理解,世俗不应该再认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是困扰人心或者是分裂世俗社会之源。原则上他们都应该遵循同样基本的前提,以及道德依据和推论的原则。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如果世俗生命伦理学是单一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也不是多元的。一个能成功体现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去除道德多元化。这种方法不是研究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有利基础,而是强调世俗生命伦理学存在的事实。因此,恩氏在本书中得出这样的论点请参阅英文版TheFoundations of Christian Bioethics,pp.15-16。:世俗生命伦理学吸引人之处是(1)因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是特定的,它是多元中的一元,决策者认为,世俗伦理因为能团结人民和避免分裂更加适合于社会,也可能是(2)因为基督教道德规范在本质上等同于世俗道德规范,因此可以由世俗哲学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样,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就既不会有分裂的危险又不会不切题意。不管哪一种可能,人们都会接受世俗的而不是特定的基督教道德规范。而且,世俗生命伦理学以它全球性宣言和普遍承诺成为最恰适的宗教选择。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这种说明似乎有利于通过瞄准从世俗道德哲学分析和争论中得到大家期望统一的目标,并使之从自身的分裂中摆脱出来。辩证思维与悲剧意识相反,虽然承认人类的种种辉煌的成就具有相对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拒绝笛卡尔理性主义所一直主张的线性逻辑顺序。基督教给于人类的不仅是一种信仰,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智慧的启示。在讨论生命问题时,只有基督教生命伦理意识可以摆脱由于浅俗而带来的茫然。人由于不能真正进入最后的精神世界,不能找回自己最后的家园,不能达到纯粹的道德准则以及实现真正合理的正义,因而人是渺小的、可怜的。然而,“人具有意识,使他能够觉察人类的一切缺欠,一切局限和物质世界的一切可能性……从不接受任何妥协,因而又是伟大的”。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我们是为思想而生的,我们的生命因为思想而变得有意义,我们全部的尊严和志趣,我们的生活动力,我们的义务都因此而发出光泽。生命不可完知,像不能理解死亡一样,我们常常充满了对宇宙的敬畏与恐惧;“耶稣在地上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种知识”同上书,原文出自帕斯卡尔《耶稣的神秘》。。耶稣是在他的弟子们熟睡时,安排了他们的得救,既考虑到他们生命的虚无,又看到他们的罪恶;耶稣认为精神是飘忽不定的而肉体又是软弱的,并且必须摆脱人以及自己往昔的朋友,才能进入真实的忧伤,这种忧伤是为生命所偿付的。我们对未来没有完整的信念,因为构成这个信念的因素许多都是我们所不可知的。生命伦理学应该使人类学会“称义”的知识,称义是学会善举之后完成救赎的成果,我们因此有权利分享公义,解除困惑,获得自由,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献上了自己。基督教的上帝观,首先并压倒一切的就是正义,正义给我们以生活的信心,正义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我们不惧怕失败,不惧怕困难,不惧怕邪恶;我们活着必须为正义而奋斗;因为我们不仅生物地生活,而且主要是思想地生活。对此,基督教生命伦理与世俗生命伦理是一致的。中国的读者应该知道,在基督精神和基督教人文思想长期浸润和融染的西方社会,把宗教伦理和世俗伦理观念达成和谐或培育道德共认意识是何等有意义的事业;恩格尔哈特教授的研究,关系着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质量和整体幸福感,更涉及一个民族的文化境况、风貌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样,对于我们这样的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笃的中华民族,也面临这样的选择和危机,虽然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理性的宗教情感和独一神祗崇拜对象,但我们从没有停止模糊地、朦胧地接受着“天道”或者“类如上帝”(As-If God)的暗示与心理召唤,尽管我们的神权观念明显功利化与较为脆弱和淡漠,但是,恩教授的这一追求和提供给我们的成果,以及他的这种探索,对我们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提醒和启示。就是说,面对这部大书,我们特别是汉语生命伦理学者,临在我们信仰极度贫困和精神极度饥渴的民族,眼下,我们最应该做些什么!关于恩氏的思想来源,也就是对其生命伦理观念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理性资源,我们分析有四个方面:(1)日耳曼古典哲学与近代哲学,除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与康德哲学外,尼采的权威虚无化以及哈特曼哲学;(2)法国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新经济思潮以及新教伦理精神;(3)基督教神学、特别是东正教神哲学、加尔文主义和地中海、波罗的海文化圈(特别是巴尔干、亚平宁、伊比利亚三个半岛的文化)的文化传统与宗教神秘主义、诺斯替文化等;(4)欧洲与北美的医学人文主义与传统、生命科学知识和医学科学技术哲学。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意在建构有限的道德相对论(或次级相对主义),虽然他经常否认道德相对主义,但他不能回避他的“部分共认意识”(overlaping consensus)与“道德异乡人”(moral strangers)理论的后相对主义内核。异乡人理论其实来源于诺斯替主义传统、犹太民族情结与希伯来文化,埃及囚虏和奴役、巴比伦之囚、筑棚与漂泊的境遇,以及地球在宇宙中悬置、生命寄居于肉身等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印痕,构成了这种“道德异乡人”观念,这既解决了避免堕入令人恐怖的道德相对主义,又表示了一种对道德多元论的包容。生活依然被我们过着——我们总是这样重复着活着,似乎没有什么今天、今生与明天、来世的差异,我们只是活,只是在过活。人们依然按时间的序列,惯性地为那些古老的仪式——仅仅还是限于仪式,表浅的、浮躁的、俗化的、物质的、情感的、喧闹的、木讷的、无意识的节日,推动着我们的岁月;神秘主义立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总是感受着一种来自于冥冥世界的压力,被挤压着生存,我知道,恩教授本人除了豪饮,几乎没有太多的爱好;此刻,我想,文本的书写是恩格尔哈特和我这样的人,在这个信仰和真理迷失的时代唯一的游戏,在这条件极其怪诞和夹带些滑稽成分的情境下,通过神秘的书写确实可以获得宗教的快乐。加尔文跟随奥古斯丁把人类整体的心理上的事情和情感的来源归为:上帝的知识和我们自己的知识。自然界和社会从此被彻底世俗化了,就此,理性和语言也被世俗化了。要到达上帝的国度,必须通过人的内在的经验和神秘的感受,而不是直接的话语。上帝通过圣灵命令给予玛丽·韦林(Mary Waring)以生命的最后力量,那是一种精神的腾飞和信仰的最后皈依,在灵魂深处,长久隐藏的“单纯的词”附丽于“真实的物”的体上,物被圣化了。参见唐·库比特《后现代神秘主义》,王志成、郑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吕克·费里不同意康德把宗教说成是人的自然秉性 (disposition naturelle ),但是他又错误的诠释了没有宗教的极端价值,吕克·费里在他的《宗教后的教徒》(Le religieux apres la religion)(周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中发表了自己对于没有宗教的社会的免于集权制的统治,审观当代社会,极其复杂的政治伦理借用于宗教的遗存,作为高压统治的基础,造成与民主力量对抗的条件,可见此时何等需要去神圣化。II不要极端的神圣化,也不可以极端的非威权主义。哲学的上帝和神学的上帝分离之后,为什么却给政治的或集权的、专制的上帝遗赠了绝好的制造灾难的空间和机会,依仗强力和严厉复仇的超越的上帝形象被统治者所替代,神灵化的人恰与人性化的神成为鲜明的对比,道成肉身反被肉身成“道”所替代,这也是宗教的大悲剧。序之末,我要说的,就是恩格尔哈特隐藏的东方正教情感的力量和文化偏好,这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恩氏习惯于或者喜欢引用圣·克利索斯托姆(St.John Chrysostom)、圣·巴西拉(St.Basil)、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本以及尼西亚与后尼西亚教父系列,还有大量的东正教神学文献。因此,有必要说明以下的这段历史断代。欧洲历史上,最具政治神学意味的争议 就算是对于公元381年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的希腊文原本的重大变动,其实这个变动是悄然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也是造成东方与西方最后互相逐出教会的根源。希腊原本中在论及圣灵“从父”而出之后的部分,并没有包括“和子”(filioque)这个子句在内: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公元850年,当东方的主教与神学家们听到这个更动后,大为恼火,以雷霆般的吼啸予以抗议,他们坚持西方的观念建立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上,这是非正统的异端的边缘的教义,迈仁多夫表述道:拜占庭人认为,“和子”的问题是东西方产生摩擦的关键。在他们眼中,拉丁教会接受内有插入文字的信经,不但抵触基督教全体大会采用作为普世基督教信仰表达的文字,同时又赋予不正确的三位一体观以教条的权威。参阅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页。这个微细的但不寻常的更动,说明东西方对于民主的不同情感,反映了那种神秘的内在的情感体验。古代西方人在没有接受基督教之先,其惯有的多神主义传统其实是一种民主的文化根基,“和子”的争论恰好反映了这种分歧的民族心理差异,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去理解。古代东方却原本是一神论,尽管后来比如华夏民族由道释的多神崇拜所替代,但还顽固地惯于皇权的奴隶性,祈望于绝对的“上帝”至高无上;如果巴尔干、小亚细亚、波罗的海文化圈和斯拉夫人承认和接受了“和子”说,上帝的绝对威权将被打破,因为必然和人子基督共同分享这个权力,而就民主主义来解释,分权的意义深刻而远大。路德与加尔文的改教运动以及文艺复兴的基础,其实就源于这种争议,尽管路德反抗的也是拉丁教会,但深刻的历史哲学根源却是令人深省的。1911年和1919年,其实与1571年一样,对中国来说,就是去神圣化的伟大运动,如果没有孙中山的神学伦理思想,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国还将是一片昏暗,没有民主的太阳照射,没有思想的解放,可怜的中国人还将在浩荡的“皇恩”下,跪着行走。非常态是为了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的常态,我们错在总用一种非常的仪式去替代生命的常态和生活的常态。或可以去偶像化不应该成为偶像的物如,我们被愚弄的心灵始终没有摆脱经意被愚弄的习性。亚伯拉罕·林肯并没有被后人作为神灵去纪念,而我们的现代所谓圣地却充斥着香火膜拜的亚宗教仪式。权威是为了维系国家秩序与公民的意志,以至于社群的向往与公益社会的权利,我们不应该被偶像所蒙蔽,我们的智慧与感悟应该在理性的制约之下,承认权威的价值,但绝不屈从于绝对的权威。上帝是西方人手中的一个概念,我们信仰主体的思想对象就是对于眼下庶民文化的一种背叛,不是对庶民本身,是对于他们精神的和信仰的拯救,使之最终寻找到心理的平静和灵性的安谧。在法语神学界,马里戎参见刘小枫选编《海德格尔式的现代神学》,孙周兴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此为《神学新杂志》中布里托的文章。(Jean-luc Marion)一直致力于表达,在上帝退出和人们不再需要敬拜偶像之后,思考作为基督人子耶稣的存在,那种贫民化和贫民的人格,并不需要海德格尔式地对基督教传统的复兴,基督是一位卓越的贫民领袖,他不是神,他值得人去纪念,是因为他离我们很近,他的崇高,不在于他的神圣,而是他只标识着人类和大自然中本应该有的本真的爱,那爱是说不尽的,是永恒的;我们到哪里去找寻没有任何利益驱动、没有任何功利的爱呢?其实,生命伦理学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中就有,它本来不独存于天堂。读罢这部译稿,我暗暗赞叹,被誉为人类文化心脏的地中海文化圈涌起的阵阵思想骇浪;其中,最先该记住589年托莱多(Toledo)的西班牙主教会议,他们把奥古斯丁在《三位一体论》一书中“圣灵从子而出”的断言,正式加在拉丁文信经中,我们这些21世纪的中国人,如何知道,去神圣化有何等意义,又是何等艰难,历史上,在“政治上帝”的暴力之下,人类曾遭遇过千百次灭顶灾祸;去神圣化要用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去换取。但不要忘记,我们只是不要那种暴力的君王,我们更需要一位给予我们民主、智慧、幸福与自由的“上帝”。为此,我的这位朋友,恩格尔哈特教授,从青年时代开始,几乎倾尽一生的精力,心向往之,用“部分道德共认意识”、“允许原则”、“道德异乡人”、“伦理序列”等,去缓释或消解人类的纷争,用“整全道德”和“真全生活”来重新确立上帝的权威性。他祈盼在一尊至高无上的上帝之下,通过多元生命文化道路,通达或最终实现我们的身体自由广场,找到一幅美好的、最能体现公义的生命政治或卫生经济政策蓝图,以造就最和谐的、平和的、大同的整全道德原则、真全生活模式与新型人类关系,这也是所有宗教、宗教徒和非宗教徒的理想,也就是我们生命伦理学道德核心价值的图示,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福祉,即应该通过我们艰苦奋斗赎回的,曾经被我们失去的、地上的伊甸乐园。最后,我愿再次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中德国诗人席勒的几句配词,结束我这篇有些冗长的序言: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怀着火一样的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威力,能把人类重新团结在一起;在你温暖的羽翼之下,一切人类成兄弟。2012年9月18日 识于南京贰浸斋
全部显示∨
译者序 生命伦理学,以圣言叙事与告诫
总序
中文版序
前言
关于本书使用圣经的说明
第一章 从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到世俗生命伦理学:全球化自由主义道德的建立道德是否专属于某一宗教?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困惑与衰落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与世俗生命伦理学:差别的消弭
道德危机以及中世纪理性的信仰
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世俗生命伦理学
启蒙运动及其晦眛的负面
对世俗理性信仰的忠诚:世俗的医学伦理和医学人文
为何一个规范的、内容整全的世俗生命伦理学不能为一般世俗条款辩护:内容需要假设
从自由论世界主义到自由世界主义:后传统的基督教背景
重新审视基督教生命伦理学
第二章 生命伦理学根源:理性、信仰与道德的合一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对道德意向工程的反思
多元主义与在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中的冲突:正当、善、特殊性与上帝
康德和他的类如上帝(As-If God)
应变的必要:黑格尔以及对道德个性的辩护
理性、信仰和克尔凯郭尔:作为一位后基督教时代的基督徒
理性、信仰和生命伦理学
第三章 作为一项人权项目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认真地内在性考量启蒙运动的遗产
知识、道德与宗教作为有限的人权项目
俗界三境:生活在一个无上帝话语的世界
作为一种框架的自由论世界主义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论世界主义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世界主义
基督教的变革:通向祛魅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
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重新审视
第四章 生命伦理学与超越:文化战争的核心异端教派、邪教、原教旨主义和传统基督教生命伦理学
从推断的根由到灵性的裂变
难以置信:一种道义选择,而非误读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心灵知识与自然法
自然、自然法和人类的堕落
作为心路历程的道德与神学知识
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和神学知识
道德神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和知识共同体
真知卓见:主教、大公会议、教皇与先知
神学的双重含义,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双重含义
嵌入时间以及人化的生命伦理学
第五章 生育:生殖、克隆、流产和分娩不和谐的节奏:传统基督教性生命伦理学与新兴世俗自由世界主义观念的共识
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有生命的伦理学
婚姻的神秘性
性行为:正确与错误的指导
亚当和夏娃的成功结合:辅助生殖
克隆、制造胚胎与胚胎利用
避孕和一个适度人口的世界
绝育、变性手术、性角色改变与遗传工程
婚前性行为、未婚避孕和艾滋病
堕胎、流产与生育
总结:有关生殖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如此陌生的缘由
第六章 痛苦、疾病、临终与死亡:意义诉求诸义何谓?面对生命有限性
死亡、诱惑和罪恶:宇宙的叙事
将医学作为偶像:放弃与中止治疗
“为什么这一切竟如此不同”
自杀和安乐死
死亡和器官移植
神迹、罪恶、魔鬼和宽恕
第七章 提供卫生保健:同意、利益冲突、医疗资源配置与宗教的整全性医学的定位:健康与寻求救助
同意、欺骗和医生:对自由与知情同意的反思
后基督时代的卫生保健
被隔离的和世俗化的基督教:宗教作为一种私人活动
基督教卫生保健制度的整全性
第八章 后基督教世界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生活在后基督教世界
索引
致谢
翻译琐记、出版的说明与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