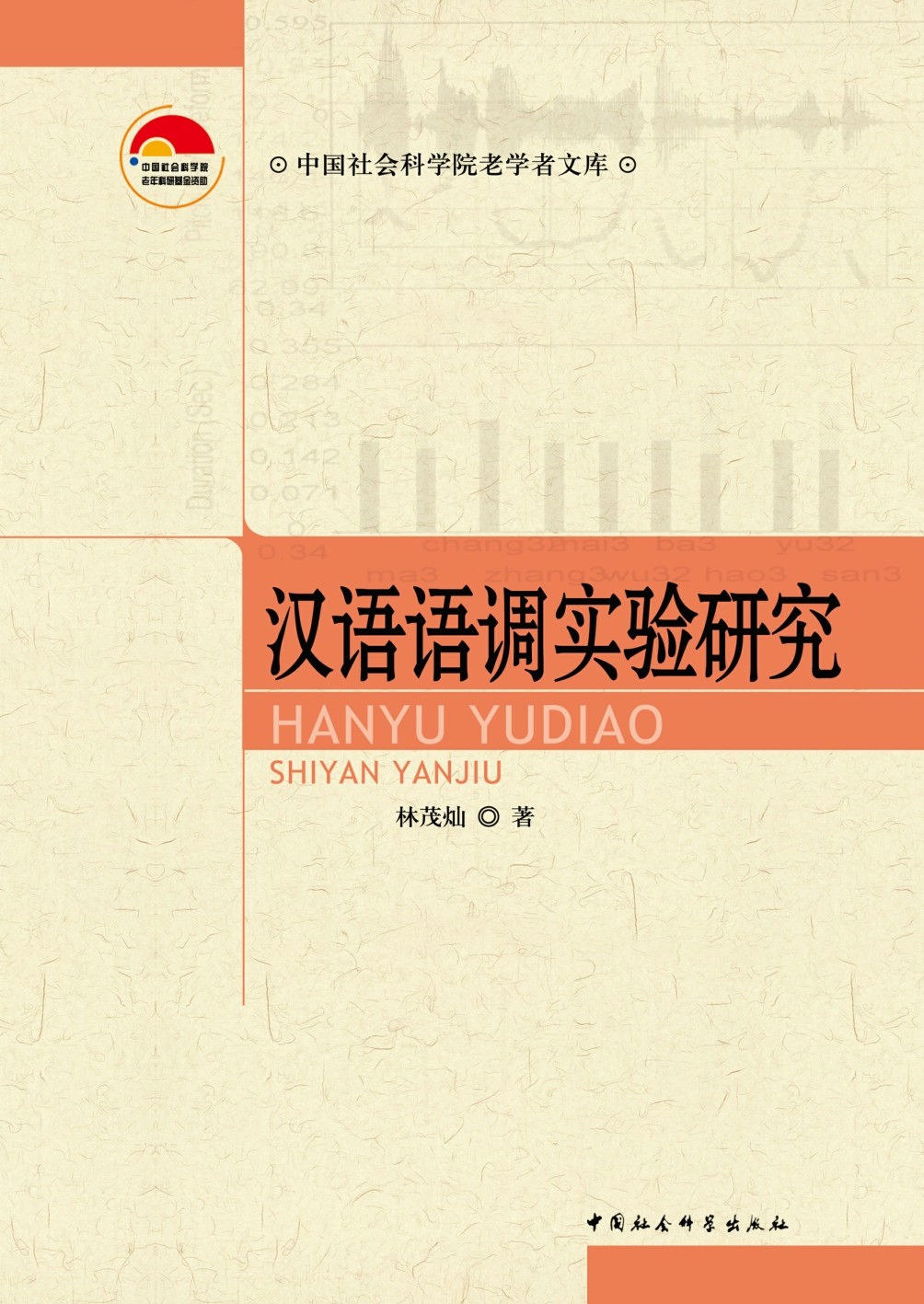本书主要内容就写到这儿。我为总结工作而写这本书,但我的心情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书中所写的结论、看法和论点,是根据我运用的语料和采用的实验得到的,难免有局限性,片面性,甚至错误,不过,出版它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因而,我殷切期待对有关问题感兴趣的先生和朋友,用更多更合适的普通话语料,用更可靠、科学的实验方法,用有关语调理论,对书中有关结论和提法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使大家汉语声调、重音、语气和语调及节奏等有深刻、全面、科学的认识,对赵元任先生语调学说做准确的概括、阐述。我在研究进程中,有些事情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回忆;我的研究得到多方关心、支持和帮助,对他们的帮助我永远铭记在心。一 音高自动提取,使我走进语音学殿堂我1958年秋季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当时叫专门化),9月30日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报到。10月2日,刘坚先生(时任语言所团支部书记)陪我到罗常培先生(所长)家里,罗先生要我研制画调器,进而研究声调和语调。10月4日,吕叔湘先生(时任副所长)在办公室见我,吕先生跟罗先生一样要我研制画调器和研究声调、语调。也在4日这一天,吴宗济先生跟我谈如何开展画调器的研制。吴先生对我说,所领导让他跟马大猷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所长)商量,马先生同意我到他领导的声学研究所研制画调器(当时我所也在中关村)。吴先生说,马先生认为研制画调器很有必要。吴先生给我一篇关于如何从语音信号中把基频提取出来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他在1955—1956年出国访问期间,在民主德国的一家图书馆复印的。我在南京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音高自动提取》,由魏荣爵先生(时任物理系主任)命题,包紫薇老师指导,我参考了有关文章,作了一些初步工作。我再次查阅了美国声学杂志上的这方面文献后,跟吴先生商量,决定主要参考他给的文章研制画调器,因为这篇文章用脉冲电路能给出较直观的音高曲线,如图1所示。1958年10月,我开始在声学研究所语言声学研究室研制此仪器,期间得到了张家马录先生(该研究室主任)及其同事的许多帮助。经过一年多的工作,“音高显示器”初步研制成功。回到所里(我所从中关村搬到西城端王府夹道5号)后,我一边改进其性能,一边开展单音节声调,和两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变调的实验研究。用这个仪器得到的研究成果有两项:一是《音高显示器与普通话声调声学特性》(林茂灿,1965);二是90年代初用当时得到的四音节基频曲线(如图1),研究了声调协同发音(林茂灿和颜景助:《普通话四音节词和短语中声调协同发音模式》,《声学学报》1992年第6期;Chinese Journoe of Acomstics,12: 213—241,1992)。刘复先生的《四声实验录》(1924)是用浪纹计记录语音波形,用他发明的乙二推断尺推算出基频曲线写成的,开创了用仪器研究声调的新时代。但是,浪纹计采用机械振动原理设计,一则不能给出语音波的振动细节,二则费时费事。赵元任先生等老一辈语言学家一直希望有一种电子仪器取代浪纹计,以深入研究声调和变调,以致语调等。吴宗济先生回忆说:“1937年,为了改进分析声调的仪器,(赵元任)派我(吴宗济)去上海找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丁西林所长,研制电动画调器等。我开始了这项工作,但因抗战发生,此工作停顿了下来。”吴宗济:《我的音路历程》,载《吴宗济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81页。因而,罗先生、吕先生、吴先生、魏先生和马先生等都对音高(基频)的自动提取非常期待、非常关切。我初步研制成的音高显示器,得到所里肯定。吴先生说,音高显示器“发现声调的开始和结尾还各有一小段的曲线,称为‘弯头’和‘降尾’。一个单字调有三个段落:弯头段、调型段和降尾段。头尾两段对于听感关系不大,但对语音合成是重要的。”吴宗济:《普通话声调实验研究四十年》,载《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73页。从“音高显示器”得到的波形和音高曲线(如图1所示),必须配以双线示波器,用一种底片平移的照相机拍摄,然后冲洗,不能实时得到所要的音高曲线,还是不方便。1978年开始,林联合先生等与我合作用数字计算机提取基频,研究字组变调(A Study of Tone-sandhi in Standard Chinese Using Computer,Proc.of the 9thInter.Cong.of Phontlic Sciences,pp.141-143,Copenhagen,1979;《普通话二字组变调实验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我们的声调研究从模拟电路进入数字计算机时代。二 接近“水声”的五年1971年秋我所接国务院调令,让鲍怀翘先生和我从河南干校回京,参加渤海石油勘探,1975年春回所。在此期间,我跟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孙林先生合作研究“水下勘探用水听器的灵敏度校准技术”。有关部门用我国自主研制的电火花震源及水下勘探用水听器(水下听音器)等,调查水下石油;我们做的水听器灵敏度校准工作,对浅海的地下石油勘探起了作用。在《中国石油》1976年第2期上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三 在吴先生带领下“走出去”,扩大了眼界,拓宽研究思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我所讨论如何恢复科研工作,吕叔湘先生找孙国华先生和我商量开展语调研究,吕先生希望我们用夏青先生的《四世同堂》话剧录音进行语调研究。孙国华和我带着吕先生给夏青的亲笔信,到广播事业局见了夏青先生。过了不久,夏青先生派人送来我们要的磁带。因为,磁带保存不好,放音质量差,更主要因为我当时尚未获得普通话语调的语感,以及当时的设备还不能实时给出基频曲线等原因,吕先生的希望和要求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而延至90年代中期开始落实和执行。1979年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ICPhS)在丹麦召开之前,会议主席著名语音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约恩荪来信邀请吴宗济先生参加此次学术盛典。时任所长吕先生提出,并得到石明远副所长同意,让我跟吴先生一起去参加,了解和学习国际上语音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参加这次语音学盛会除吴先生和我外,还有声学所张家马录(见图2),张家马录先生参加会议一切费用都由社会科学部负责,说明我院、我所领导非常重视此次学术活动。吴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他的共振峰简易计算法(《声学学报》第1卷第1期),并当选为国际语音科学会议的终身常务理事。我们三人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参观学习的一切活动,都由两地大使馆安排。我们在吴先生带领下,会后参观和访问了歌本哈根大学语言学系和B.K.声学仪器公司,然后到瑞典访问,在瑞典期间主要参访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还访问了Eric电话公司。我们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跟方特(Gunnar Fant)教授领导的“语音、音乐和听觉系”同行举行多次座谈。方特教授等学者关心我们的研究工作,多次对我的工作提出看法,建议我在研究声调曲线的“弯头段”和“降尾段”时,应该进行感知实验;他们非常重视在语音研究中采用感知实验方法。由于他的建议,我后来的不少工作在声学分析基础上,都加上“听辨实验”和“感知实验”等方法,使研究结论更可靠。图3上部是一张他们拍摄的方特跟我谈话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标题是《我们看到的方特,大家喜欢他》,刊登在该系为庆贺方特教授六十大寿出版专刊的首页上。吴先生和我又参加了第十届(乌特列支,荷兰,1983),第十一届(塔林,原苏联,1987)第十二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艾克西—普鲁旺斯,法国,1991)。我还参加了第十三届(斯德哥尔摩,瑞典,1995)和第十四届(旧金山,美国,1999)国际语音科学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我参加的第十三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这次学术活动是语言所领导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之间签订的协议,作为学术交流而进行的。我提交论文是:《普通话两音节间基频过渡及其感知》。论文被安排在全体会上宣读。会后,我到皇家理工学院语音通讯系和隆德大学语音学系访问,期间方特教授和葛丁(Eva Garding)教授跟我详细介绍、讨论大会主题之一“语调”,使我对当时语调理论的发展有了进一步认识。会后,应法国尼斯大学邀请,我到那儿学习和访问了三个月。在梅山乐博士和葛尼博士帮助下,我听辨了他们收集的普通话语调语料,做了一些分析,并收集不少英语等语调的资料。1993年我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工作三个月,1997—1998年度,我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做学术访问,我分别在李行德教授和徐云阳教授领导的语音实验室,正式开始了普通话语调的实验研究。(日本语音学家、言语工程学家藤奇博也教授拍摄)吴宗济先生在提出变调块及其移调主张的同时,1982年(《汉语语句中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明确地说:“如果字句跟平叙句完全相同,而是用来提问,则句尾调阈可以提高。即使句尾的本调为降调(去声)时,调尾的频率也会提高一些,但拱度(调型)不变。”吴先生关于汉语疑问语气的这种看法,极大地启发了我,促使我深入钻研赵元任语调论述,应用自主音段—节律(AM)理论,并吸收调群理论中的调核思想,开展普通话语调研究。2004年3月末为庆贺吴宗济先生95大寿,我所举办关于“音调”的国际研讨会,我被安排在全体会议上报告《汉语语调的边界调产生与感知》(英文)。方特教授会后问我,“汉语语调除了边界调外还有什么东西”,我回答,“还有重音”;他继续问道,“你的重音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我说,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词重音,接着研究韵律结构,现正在研究句重音。他在2005年末来信说,希望我到他那儿合作研究汉语语调,在边界调和重音基础上,加上一些规则,从而得到实际的音高曲线。不料,2007年年初他来信说,他犯病了,研究工作需延后进行(见他给我的短信,图3下部)。不幸的是,他于2009年6月间离世而去。我失掉一位良师益友!我研究语调从声调入手,然后探讨词语的超音段问题,包括词重音。我先研究赵元任说的中性语调,因为它是语调基础,然后研究句重音,直至语气,最后又回到重音。四 感恩与致谢我在语言所里工作了50多年,得到历届所领导的培养、关心和支持。这本书是我50多年在语音学超音段方面的研究总结。我把这本书奉献给关心和支持过我研究工作的前辈、领导和同行。前面提到和没有提到的领导和前辈要求和希望我研究声调和语调,但我工作做得太慢了,而且还有缺点甚至错误。我把它出版是便于大家批评指正。2007年春节期间,吴先生对我说,后年(2009年)是赵元任《北平语调的研究》(载《最后五分钟》,中华书局1929年版)发表80周年,可否做个实验看他的“代数和”是什么。过了几天,我把我对“代数和”的理解和研究计划告诉他,他同意我的理解和计划,随后我就开始实验。这个实验结论是,“疑问边界调基频曲拱的音阶比单念这个边界音节声调的高,陈述边界调基频曲拱音阶比单念这个边界音节声调的低”,证明了赵元任先生关于声调与语调的代数和思想的科学性。我2009年底写完初稿给吴先生看,希望用两个人名字发表。他说,这次合写文章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关于“音高显示器”文章,当时他是应该署名的,因为完全是用他提供的材料,在他指导下完成的。我们几位同事,在吴先生主持和率领下,于199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实验语音学概要》,这本书没有涉及语调问题。吴先生多次催我以出书方式把工作总结一下,只是我写得太慢太慢;不幸,他身体于2009年开始不好。我这本书的序言本应该由他写的,现在他走了,我对此十分遗憾!这本书的许多工作是跟严景助先生和孙国华先生共同完成的;语音研究室李爱军主任让梁红丽同志帮我标注语料,整理些数据。熊子瑜博士为我编写韵律标注及编写作图程序。我还经常请语音室同仁讨论问题。我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立后,我的有关研究课题就得到它们的资助,再次表示感谢。本书撰写和修改过程,王理嘉教授、鲍怀翘研究员和李爱军研究员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张林先生及有关编辑人员,只用半年时间出版了我的这本书。这本专著不仅图表多,而且图的类型多,较复杂。对张林等先生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深表感谢。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的资助,十分感谢。我进入大学和语言所以后,父母给了我八个字,我一直奉为座右铭,其中四个字是“困而学之”。我努力在实践中学习,我努力学习有关书本知识,学习同人的经验。我用这本书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我是努力工作的,虽然还有许许多多缺陷。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也感谢我妻子和儿女家人,没有她们的鼎力支持,我的工作难以完成。林茂灿于北京华威西里寓所2010年11月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