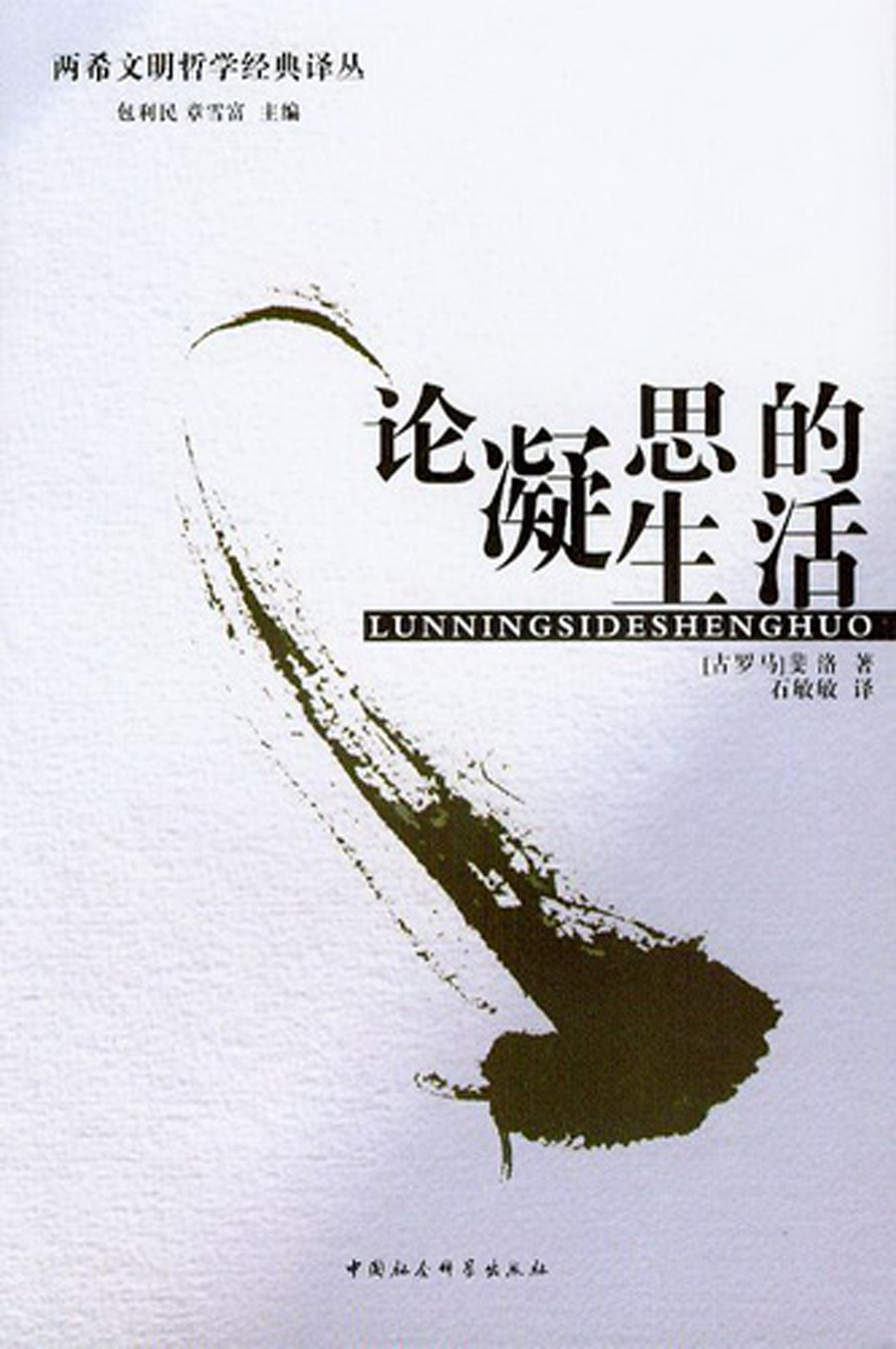一
就所谓“宗教”这一对象的理解而言,诚如史密斯先生所洞见的那样,在相当意义上,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现象,宗教本身可以具体理解为一种由“个体的信仰”与“累积的传统”叠加起来的人类文化系统。就此而言,所谓“宗教”本身实际上包含着既互为表里、又相互依存的内外两个层面。其中,个体的、内在的“信仰”经验是宗教精神及其外在表现的核心或起源。与之相比,作为一种“累积的传统”的那些宗教形式,不过是这一个体的、内在的“信仰”在外在历史或精神世界中的某种折射或沉淀。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较之其他民族的历史及宗教经验而言,历史上犹太民族集体被流放的特殊民族经验,最终致使所谓“犹太教”这一犹太人的宗教形式,在犹太宗教—文化或文明这一外在的、累积的传统中,占据了几乎全方位的、主导性的历史地位。从“宗教”这一包含了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传统”的特殊文化系统来看,所谓的“犹太教”或犹太宗教—文化这一系统,至少在近代之前,事实上并无绝对的宗教与世俗之分。
究其原因,在所谓“宗教”这一文化系统中,正是内在“信仰”在这一系统中源发性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使之最终成为外在、累积的传统或规范的根本源泉。换句话说,正是这种内在、纯粹的“信仰”本身,才是一切外在传统或规范最终得以“神圣化”的根本性依据之所在。显而易见,对于犹太教而言,在宗教之内在的“信仰”层面,犹太教神秘主义这一内在“信仰”经验及其在历史世界中的实践和传统累积本身,才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性宗教—文化系统的“犹太教”,在犹太历史上最终占据特殊的、主导性历史地位的内在根本依据。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犹太神秘主义者在犹太历史生活中的存在,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赶不上犹太教中《圣经》及其“此在”性衍生物《塔木德》传统的影响,然而,我们除了不应忽视《圣经》本身在内在灵性向度上的丰富内涵之外,最好也不要忘了平哈斯拉比关于《佐哈尔》这部《圣经》诠释之作内在价值与历史地位的那句名言,在犹太民族集体性被流放的苦难岁月里,正是《佐哈尔》才可以帮助他“继续做一个犹太人”。究其根本,在纯粹信仰意义上,较之“此在”间历史世界中的传统或规范性延伸,《圣经》之为《圣经》的根本,首先还在于其内在的信仰层面上的“神圣性”。
历史上,犹太教神秘主义对历史世界中犹太生活的具体影响,因为早期神秘主义者在宗教灵性实践中,其主要兴趣或关注目标集中在前历史的创造时期或后历史的救赎时期,即历史存在的起点或终点,因而在直到15世纪后期的前三个时期里,较之拉比犹太教和《塔木德》作为正统性规范的地位与影响,犹太神秘主义的地位与影响总体上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宗教神秘主义者的秘传传统,特别是犹太历史本身所独有的流散性特征对这一神秘主义传统发展的外在影响,致使犹太神秘主义在作为一种外在、历史的整体性观察对象之际,在相当程度上,明显具有历史脉络上的一种“断层感”。惟其如此,正如前文所述,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所谓的“犹太神秘主义的遗产仅仅是成千上万被人所忽视、更从未被阅读过的中世纪手稿”。而索伦教授的开创性贡献则是“从面对一堆散落杂乱的、不成篇幅的页码开始,并将其最终转换成为历史”。
尽管如此,较之这一历史层面的表象化结论,值得注意的是,犹太教神秘主义自其出现伊始,事实上就并非犹太教中一种边缘性角色。理由在于,历史上的神秘主义团体虽然试图在他们获取的神秘知识与大众之间保持距离,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同时也是正统犹太教社会中的核心成员。《宫殿书》与默卡巴神秘主义著作以拉比阿基巴、以实玛利和其他《密西纳》时代先知的托名出现,本身就暗示这些神秘主义信徒在思想或文化上,并非处于远离《塔木德》和《米德拉西》传统的边缘地带。再者,中世纪阿什肯那兹“虔诚者”运动的推动力,主要来自莱茵地区最显赫的卡罗尼姆斯(Kalonymus)家族,而狭义上最早的喀巴拉学派,普罗旺斯的亚伯拉罕·本·大卫拉比学派以及纳蒙尼德(Nahmanides)为首的西班牙格罗纳学派,都是那一时代哈拉卡学术的先锋,同时其领导人也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在此背景下,考虑到正统犹太教中《塔木德》和《米德拉西》文学对神秘知识的普遍引用,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古代后期至少有一部分正统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及拉比学者,都同样对神秘主义实践抱有浓厚的兴趣。换一种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正反映了神秘主义作为宗教当中的内在“信仰”元素,相对于外在“传统”或规范之衍化的灵性根本地位。
在犹太教历史上,宗教神秘主义对犹太社会及宗教文化的影响在12世纪后期逐渐显露出来。当时,喀巴拉神秘主义信徒所做的许多道德短训虽然并不反映他们的神秘观点,但至少说明他们认为普通的犹太民众可以并且应当接受这些说教,并且开始逐渐放弃过去所坚持的秘传传统。历史上,中世纪阿什肯那兹犹太人中的“虔诚者”以及西班牙格罗纳的喀巴拉信徒,都曾创作过一些对当时的犹太文化极富影响力的道德伦理作品,诸如“虔诚者”本人耶胡达的《虔诚者之歌》,以及约拿·格隆迪(Jonah Grondi)拉比的《悔恨之门》(Sha’are Teshuvah),等等。随着《佐哈尔》的传播,特别是在西班牙大驱逐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后,从公元16世纪起,喀巴拉信徒开始公开出版充满神秘象征术语的喀巴拉道德作品。至公元17世纪,也就是最终导致萨巴泰弥赛亚运动出现的那一个世纪中,这种神秘象征主义表达方式,业已在希伯来布道文学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概而言之,依靠神秘主义道德作品这一载体,喀巴拉最终逐渐渗入犹太人的日常宗教和道德实践当中,并在17至19世纪中开始演变成为犹太宗教文化中的主导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在于,喀巴拉的神秘主义诠释赋予传统宗教戒律与道德标准一种魔力般不可抗拒的价值或意义。与之相比,18世纪兴起的近现代哈西德宗教运动同将犹太个人生活的彻底“神秘主义化”,在更为内在的灵性实践意义上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并最终将之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巅峰。
二
在人类宗教历史上,犹太教神秘主义形式喀巴拉显然占有一定的重要位置。就这一犹太教中所特有的宗教神秘主义实践及其相应的文化体系而言,其在思想性起源或表达形式上所受到的影响,除了自身历史上《希伯来圣经》等宗教经典中的神秘主义资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性流放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历史上,犹太流散生活对喀巴拉神秘主义具体形态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正如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喀巴拉宗教运动所表现出的明显的地域性缘起特征,不同时期的犹太神秘主义在宗教思想资源上,无疑深受不同流散地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中外来宗教及哲学等传统的影响,历史上的诺斯替教派、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以及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等诸多宗教或哲学流派思想,都对特定时代的犹太教神秘主义思想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历史性影响;其二,在流散生活中,不同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运动大体上萌发于不同的历史时空里,因而其所侧重的具体表现形式,实际上也一直深受这一特定的不同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无论是默卡巴信徒的“飞升”,中世纪德国哈西德的“虔诚”,还是近代东欧哈西德运动中的所谓迷狂或喜悦,所有这些不同时期犹太人灵性运动中所凸显的重要特征,事实上都确定无疑地对应着特定历史时期犹太流散生活中的内外生存环境。换言之,神秘主义作为一种相关内在信仰体验与实践的累积传统,在特定历史时空内,其所关注的重点及其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也都深受不同外在历史性生存环境的影响。
民族性流散生活对犹太宗教发展的这一影响,甚至可以从喀巴拉神秘体验中人—神之间的关系定位上反映出来。
历史上,虽然有早期的《宫殿文学》和默卡巴神秘主义,以及阿布拉菲亚等的灵性迷狂经验,但总体而言,在喀巴拉神秘主义实践中,个体灵性经验中的入神体验就其重要性地位或历史性记载而言,较之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宗教神秘主义,显然处于一种不是那么非常重要或突出的位置。概而言之,在犹太教神秘主义灵性经验中,除了后期卢里亚喀巴拉神秘祈祷中的与神“合一”(Yihudim)外,人—神之间即便在神秘体验的最高阶段,大体上都仍然被描述为一种“与神相依”或类似的灵性状态或关系。换言之,在喀巴拉神秘主义历史上,“神性”与人性之间即便在最高的相遇中,都竟然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二分状态,更不可能出现苏菲神秘主义历史上诸如“我即真主”那样的极端神秘经验。事实上,今天的人们大体上可以认为,在西班牙大驱逐这一灾难性事件之后的喀巴拉神秘主义发展历程中,似乎已看不到太多纯粹独立的、个体性的神秘体验,而更多只是围绕历史世界中现实与命运问题所作的一些神秘主义范式的象征性阐述。导致这一历史性现象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在卢里亚喀巴拉之后,实际上,犹太神秘主义大抵上并不突出或强调宗教体验之“神圣”向度在“此在”之历史世界中的全然贯通。从原因上看,这一历史态势的形成无疑与喀巴拉对流散生活的历史性关注或选择密切相关。
在犹太宗教生活中,喀巴拉神秘主义重要历史地位的形成,就其作为一种宗教之内在源泉的本质而言,源于其在相关民族性流散命运与生活上,大抵不同于拉比犹太教主流上所秉持的策略或立场。
概而言之,较之历史上拉比犹太教对民族性流散生活总体上所采取的适应与安抚政策,对于喀巴拉神秘主义而言,神秘主义在信仰意义上的“神性”本质,就已经决定其不可能完全屈从于历史世界中的有限性,不可能全然接受或容忍一种民族性的被奴役、被压迫的非人道生活,这样一种不公不义的民族性历史命运显然有违“神”的公义与仁爱。就此而言,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样,在犹太教神秘主义中,所谓犹太“灵性”的最根本体现即在于犹太人,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民族本身,对于上帝“显现”或“临在”之生活的终极追求。从根本上说,犹太神秘主义“灵性”诉求中所体现出的这一终极内涵,实际上也同时是犹太教作为一种文明的信仰核心。在这一宗教信仰体系的灵魂最深处,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宗教和信仰意义上,绝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内在”或“内向”的灵性生活,而是努力实现“神性”本身在历史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的最终统一。在此意义上,历史上的喀巴拉神秘主义,无论在不同历史时段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制约或束缚,其实都始终本能地蕴藏着一股不可抑制的宇宙洪流。
较之其所蕴藏的这一内在的、本质性的“神性”力量之源,历史上的喀巴拉神秘主义在“此在”间践行其“神性”使命的历史过程当中,恰如卢里亚喀巴拉的创造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上帝的“神光”在流溢过程中受到了犹太流散生活的延滞与阻碍,乃至坠入“黑暗王国”的深渊。在犹太教历史上,喀巴拉神秘主义最终与拉比犹太教之间达至和解与妥协,并以神秘主义的方式为拉比犹太教及流放生活中的“托拉”提供某种“神圣化”的合法性背书。借此,在现实历史层面中,喀巴拉最终成功实现自身在犹太宗教生活中的所谓“正统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在于,在历史世界与“神圣世界”之间,喀巴拉神秘主义事实上大抵并不直接鼓励,甚或说刻意回避在“此在”之历史世界中追求实现“神性”意志上的公义与完满。在此过程中,历史上的喀巴拉神秘主义实质上更多偏向于某种退而求其次的历史主义选择,不是单纯鼓励从“神圣”维度淡化或超越“此在”历史世界中的苦难与痛苦,就是片面强调从“此在”历史世界中的苦难与痛苦中“发现”其所蕴含的“神圣”价值或意义。就这一历史性的实践选择而言,喀巴拉神秘主义在大多数历史时段所作出的这一历史主义选择,一方面固然有益于缓解漫长流散生活中“未被救赎”的痛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其发挥与拉比犹太教相类似的“正统化”身份与作用的同时,这种历史主义选择与内在信仰本身所直面的“神性”召唤之间所存在的持续的尖锐冲突,也使得历史上喀巴拉信徒的生活和行为常常不得不处于永恒的背叛当中,尽管这一困境的根源,说到底,都是民族性流散生活及苦难命运在历史世界中的必然反应。
三
在犹太神秘主义历史上,最能体现喀巴拉与犹太历史经验间特殊关系的一个明证,就是喀巴拉与犹太教“救世主”—弥赛亚信仰之间漫长而曲折的互动关系。
从历史来看,犹太教最初关于救世主“弥赛亚”的信仰仅仅是一个历史范畴,换言之,从宗教灵性的体验意义上来看,在这一最初的弥赛亚信仰中,内在“神性”维度上的拯救及“救赎”成分事实上并非一开始就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犹太教中,《希伯来圣经》虽然赋予犹太人的“救世主”弥赛亚观念一种“神圣”的宗教气息,但这一时期的“救世主”期盼实际更多与历史世界中关于民族性放逐与获救的现实性诉求层面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一几乎全然历史主义的民族性诉求,历史上流散生活中正统的拉比犹太教实际上非常恐惧并担心犹太民众的这一现实心理诉求,在日常宗教生活中,他们事实上并不鼓励关注来世或惩罚,对“救世主”弥赛亚时代到来所需准备的必需条件,正统犹太教除了笼统地认可“大卫之子”将在全恶或全善的时代到来这一说法之外,实际上并无其他更进一步的准确支持。与之相反,正统犹太教拉比们所坚持的关于实现历史主义救赎或解放的三条“誓约”或“禁令”,却成为犹太历史上阻碍犹太人实现民族性拯救与解放的最大障碍之一。
较之正统犹太教的这一实际立场,历史上犹太教神秘主义对于弥赛亚信仰的推动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虽然这一贡献本身自有其神秘主义灵性底蕴先天无法回避的悖论特质。
较之拉比犹太教对于弥赛亚信仰的躲避或恐惧心态,历史上喀巴拉神秘主义首先使犹太弥赛亚信仰具有了彻底的末日论的超验性质,尽管不同流派的喀巴拉诠释体系无论赋予犹太人这一祈求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来说,都首先需要从“神性”层面上内在灵性救赎的角度来阐释自身关于这一犹太信仰的支持。卢里亚喀巴拉的神秘诠释,一方面,在宗教的内在精神层面上,赋予救赎本身宗教合法性上的“神圣化”支持;另一方面,更间接肯定了宗教的内在救赎和历史的外在救赎之间的一致性。其后,萨巴泰宗教运动则以戏剧化的悖论方式,强化了卢里亚学说对于内外救赎一致性的神秘主义合法性支持。最终,18世纪的哈西德运动虽然背弃了这一危险假设,却通过“神秘主义”的大众化,使弥赛亚信仰成为犹太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现实结果如何,历史上积蓄已久的犹太弥赛亚信仰,最终通过神秘主义诠释在宗教合法性上的“神圣化”支持,缓解、释放了犹太人在宗教心理和现实历史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较之喀巴拉对犹太弥赛亚信仰这一颇具悖论色彩的支持,人们不难发现并理解,作为宗教生活中信仰之内在精神最纯粹的代表,喀巴拉历史上对弥赛亚观念的神秘诠释同其对犹太律法的理论诠释一样,实质上都不可能去除其灵性精神中内在、超验性的宗教特质。就此来看,在喀巴拉神秘主义这一“神圣化”范式的支持或鼓动之下,犹太弥赛亚信仰中宗教的内在救赎与历史的外在救赎之间的悖论关系,夸张体现为现实生活某种凸显的对立或张力。从这一点来说,正如索伦教授指出的那样,弥赛亚信仰不仅仅反映了犹太教历史观的基本层面,理解其发展史中的辩证法,更意味着理解犹太教对自身及社会、甚至宇宙历史的观点。一句话,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参与与支持下,犹太教中的弥赛亚信仰最终完美体现了宗教神秘主义视域中关于宇宙或存在的灵性实在维度。作为一种具备神秘主义超越性与内在性的认知结果,历史上,犹太教弥赛亚信仰阻止将“未被救赎”时代的任何人类业绩看作是存在的最终结果。对它而言,人的一切都是暂时性的、第二位的,一切将有赖于最终的“救世主”弥赛亚的到来而得以改变。这是神秘主义向度中存在与原则上反存在的弥赛亚思想之间一种辩证的紧张关系。
正如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其实不难想象,犹太教要突破这一悖论,将关于救世主的弥赛亚思想带入作为“存在”之一部分的历史世界中,其代价是沉重的。考虑到这一结论,显而易见的是,历史上犹太教关于“救世主”弥赛亚的拯救与解放信仰,正如我们以往所分析的那样,在大多数情景下,其实并不涉及所谓“赎罪”这一内涵,虽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使用“救赎”这一带有某种强烈的基督教意味的术语。在此,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尽管后者原初只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分离派别。从历史观点来看,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在弥赛亚信仰上的这一方向性差异,说到底还是缘于犹太民族历史上特殊的流散经验或遭遇。概而言之,在关于民族性悲惨命运的宗教诠释原则上,如果纯粹将历史上全民族的三次流放在“神性”意义上解释为某种集体性的“有罪”惩罚,并由此而将关于弥赛亚拯救的信仰观念理解为一种“赎罪”行为或历程,那么,这样一种宗教诠释本身无疑既是对历史性苦难命运的漠视和对民族性心理诉求的打击,亦有悖于以色列上帝的公平与正义。历史上,喀巴拉与犹太弥赛亚信仰自《佐哈尔》时代以来愈来愈密切的历史关系,既是对这一历史事实与背景的最好说明,也是13世纪末出现的《佐哈尔》之所以能够最终成为犹太教三大宗教经典乃至喀巴拉历史上最伟大著作的根本原因,因为它在冥冥之中,以自身特有的宗教灵性方式,帮助他们“继续做一个犹太人”。
四
相比于犹太历史命运面前的艰难选择,在喀巴拉与犹太弥赛亚信仰的历史性互动中,犹太教神秘主义在近代东欧哈西德运动的迷狂与喜悦中,最终彻底突破了宗教神秘主义历史上所秉持的秘传原则。在哈西德圣徒或领袖这一灵性媒介的沟通下,历史上喀巴拉第一次公开实现了“神秘主义”的“大众化”,乃至成为布伯所言的一种“民族精神”。在此基础上,经历了二战中纳粹大屠杀的磨难与考验,战后哈西德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在现当代哈巴德哈西德教派的宗教思想中,物质与精神之间开始连接并贯通,而喀巴拉秘传知识的公开化更有利于真正的信仰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在哈巴德宗教运动中,不仅“犹太人都是哈巴德派”,并无宗教或世俗之分,而且喀巴拉奥秘的传播已从宗教犹太人和世俗犹太人的民族性宗教范围,扩展至超越民族性宗教局限的世界其他民族当中,或许这也是犹太教历史上喀巴拉神秘主义最有生命力的一次飞跃。
历史上,犹太教神秘主义对犹太人及犹太生活最为深刻的影响,无疑是精神和灵魂层面上的。
从喀巴拉信徒所体验的宗教灵性维度而言,犹太人所置身其间的“此在”之历史世界,究其根本,不过是“神性”创造之“神圣世界”的某一映射或投影。就此而言,对于信仰的真正拥有者而言,在存在之绝对或终极维度上,所谓“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划分,不过是“此在”之历史世界间人类有限经验中的某种幻影或假象。在此意义上,正如布伯在近代哈西德运动研究中所洞悟的那样,在纯粹信仰意义上,哈西德运动对于“神性”无所不在之内在性的坚持,以及信仰者个体在此维度上的灵性领悟,才是“真正带有犹太人创造性天才印记的深刻思想”,也是这场灵性复兴运动对犹太文化真正精神的继承及价值之所在。由此出发,也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犹太民族中的宗教普世主义者何以始终矢志不移地坚信,犹太人必定是永久的流浪者,“因为以色列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换句话来说,“犹太人在空间没有根,他们的根在时间之中……他们的祖国是历史本身。”迄今为止,在“神”所永驻的绝对世界里,犹太人在宗教、历史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及其历史贡献亦在于此,而喀巴拉神秘主义对此犹太精神和灵魂的贡献也同样集中于此。
至此,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卢里亚喀巴拉在创造问题上所正确阐释的那一起点:既然上帝在自身之内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作为“神”的信仰者,问题的根本则更在于,在“此在”间坚守“无限者”在“神性”之内在与超越上的终极统一性。在此意义上,对于犹太人以及锻造其灵魂的喀巴拉神秘主义而言,我们可以借用那位学者的话来说,“故事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成为历史,它秘密的生命力明天会在你或我身上爆发出来”,虽然“看不到的神秘主义之流会以什么面貌再次出现,我们并不知道”。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在相关喀巴拉在内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研究”当中,正如哈维在前面所明见的那样,最为根本的,其实并不在于“此在”间所谓历史的“事实”或“哲学”的观念,更不是相关神秘体验本身有限记述的哲学化辨析或臆想,而是信仰本身所面向并领悟到的隐秘、内在并超越于尘世间这一有限历史世界的“神圣”存在与生活。唯其如此,在“此在”之现世生活里,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才能借由“此在”间的不懈努力,超越形而下研究局限之羁绊,在存在的终极向度上,发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尊严和勇气,而绝非仅仅只是“在生活的某些体验中意识到上帝”。在相当程度上,这既是信仰主义与俗世主义生活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也是人类历史上不同群体之间在文明意义上往往存在着令人惊悚的巨大沟壑的实质性原因之所在。